第四章 印度文明的确立 (至公元前5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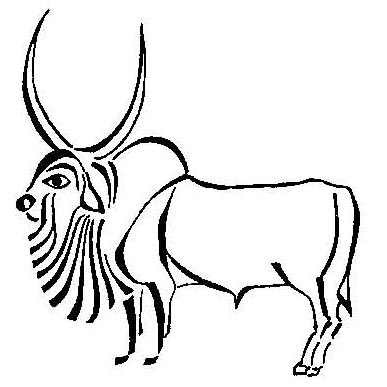
公元前1500年左右好战的入侵者摧毁了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开启了印度历史上的黑暗和野蛮时代。向南穿越山区的几轮雅利安入侵者可能耗费长达300年时间才完成迁徙。在此期间,互相敌对的武士群体赶着牲畜四处漫游,时不时停下来收获作物,然后再次踏上旅程。这些四处迁徙的人互相争斗,征服他们遇到的任何土著人口。游牧民族逐渐渗入印度的新地区,传播雅利安语言,打破内陆森林地区各民族早期的孤立状态,雅利安人因其尚武精神和更好的武器轻易地征服了这些森林民族。
但是,游牧民族开始逐渐定居,过上更稳定的农业生活。畜牧业不再像游牧和征服的英雄时代那样享有突出的地位。更繁重的田间劳动充实了武士牧人闲暇的日常生活。但即使入侵者完全过上农业生活后,雅利安人向印度南部和东部的扩张也未停止。他们的刀耕火种耕作方式要求在旧耕地变得杂草丛生时不断向新土地迁徙。
印度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留下的遗迹很少。由于缺乏设施良好的城市或永久性的居住地,考古学者未能发掘出多少早期雅利安人的遗存。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时代留下了文献。但这些文献的保存应该归功于后来的祭司对它们作了改编并应用于宗教仪式。在此过程中,原始文献在被一代代口传心授时经过了多次变化。结果,我们常常无法知悉哪些是真正的古代文献,哪些是后来增添的内容。但是,最神圣和现存可能最古老的梵文诗集《梨俱吠陀》和大型史诗《摩诃婆罗多》,包含了描写贵族弓箭手如何驾驭马拉战车驰骋疆场、用密集的箭矢与敌方的英雄展开殊死搏斗的段落。这些段落证明,像希腊和中东一样,印度也经历了贵族战车时代。
大约公元前900年,战车战术不再流行于印度。铁器传播到南亚次大陆,像中东地区一样,铁器使那些无力购买战马和战车的穷人也能用盔甲保护自己。因此,铁器时代的来临,打破了贵族的支配地位。随着铁器改变战场上的力量平衡,小城邦兴起,在这些城邦内,每个战士都有权参与政治决策。这种武装的、原始平均主义的群体存在的证据主要来自北部,尤其是喜马拉雅山的南麓;但是在恒河流域中央集权的大型君主国开始取代这种地方群体之前,同样的政治结构也可能曾经更广泛地分布于其他地区。的确,只有当这些古老的氏族共和国臣服于一些伟大国王的武力后——这个过程在大约公元前600年达到顶峰,我们才知道它们的存在。
向恒河流域的转移
铁器对印度生活还产生了另一个重要后果。用这种新金属制作的工具加速了对丛林的砍伐,特别是在恒河流域,季风带来的大量降雨使那里的植被非常茂盛,如果树木被砍倒,那么它的土壤可被开垦为非常肥沃的耕地。正如我们看到的,可能最初由东南亚耕种者培植的水稻大大提高了恒河流域的农业产量。中东农业的两大作物小麦和大麦的亩产量大大低于水稻。因此,适宜种植水稻的地区,能养活更稠密的人口。随着水稻的种植,人们开始长久地定居在特定的土地之上,因为通过根本改变土地的湿度,稻田的人工灌溉和排涝几乎清除了所有的杂草。此外,为了引水到稻田而需要的围堤、挖掘和平整工作太耗费劳力,因而迁徙到新地方定居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于是,水稻种植盛行的结果是,全面定居的农业、永久性的村庄与城镇中心,以及因无法逃进丛林中的空地而容易被征税的人口,都兴起于恒河流域。
因此,到公元前800年,恒河流域取得了文明复杂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充分条件。印度河流域这次落后了许多。古老的迁徙种植方法在印度河流域仍然普遍存在。每当国王的税吏征税或摊派劳役时,当地人就在森林中逃得无影无踪,在他们之上不可能建立起任何坚固的大规模政治体系。相反,在东部,稻田既把种植者固定下来,又给予他们一种高产量的农业,这种农业使他们能够在交出大量粮食之余生存下来。
因此,由职业行政人员和职业士兵维持的几个大君主国开始在恒河流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印度河流域(很可能还包括我们一无所知的印度南部)仍然分裂为众多的部落集团,即使统一,也只是与某个强大国王结成不稳定的宗主关系,在亲信追随者的小圈子外,这些国王缺乏真正的管理权威。但是在恒河流域,有效的中央集权君主制的发展支持了宫廷中心的兴起,在宫廷里,高级手工业技巧得以迅速地发展。地区之间的贸易也变得重要了,甚至从恒河流域的中心向四周辐射,为印度河流域的生活增加了新的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考古材料表明,到大约公元前800年,印度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海上贸易又恢复了。
从这些方面看,印度的发展与中东地区相当,只是稍微晚一点儿,文献记录稍微少一点儿。但是公元前800年后开始出现于印度的新的生活方式,与兴都库什山以北和以西的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盛行的大同主义世界大不相同。新兴的印度文明的独特性集中体现于种姓制度和印度宗教对禁欲和先验的强调。这两个特点都需要稍加解释。
种姓
现代种姓制度是共同饮食、内部通婚并严禁其他人参与这两项亲密活动的集团。此外,任何种姓的成员都必须佩戴一些独特的标记,以便他人知道谁属于、谁不属于这一种姓。随着不同种姓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在其他种姓面前如何举止的明确规则也成为必需。当整个社会最终都以这些原则组织起来时,任何陌生或入侵的群体都自动地变成另一个种姓,因为其他人口的排外习性必然在就餐和通婚方面把新来者排除在外。在一些争端中,或者仅仅通过一段时间的地理分隔,大种姓可能很容易就会分裂成小的集团。新种姓能够围绕新的职业而形成。在社会中找到新生计的流浪者和背井离乡者受到周围种姓习惯的约束,被迫一起吃住、相互通婚。
至于印度社会如何或何时根据这些原则被组织起来,仍不清楚。也许印度河流域文明本身就是建立在类似于种姓原则的某种制度的基础之上。也可能雅利安入侵者与被他们征服的黑皮肤民族之间的互相仇视为后来印度的种姓制度打下了基础。但是无论种姓制度的起源是什么,后来印度人的思想和感情的三个特点都被用于维持种姓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仪式纯洁性的观念。由于担心会因与低级种姓接触而受到玷污,所以“不洁的”种姓为婆罗门种姓和其他接近金字塔顶的种姓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去限制与低级种姓的人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