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1500~1700年的远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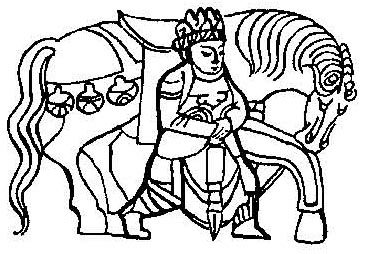
1513年,第一位葡萄牙商人抵达南中国海岸,明朝政权已经开始显示衰落的中国王朝的典型病态。沉重而分摊不均的税收,加上宫廷阴谋,导致各省爆发零星的起义,来自草原和海上的入侵正日益加剧。明朝军队人数众多,装备精良,如果指挥得当,他们就能够很好地证明自己的实力。例如,1592~1598年,明朝军队帮助朝鲜打败了日本两次可怕的入侵,尽管日本军阀丰臣秀吉竭尽全力。在海上,明朝水师也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胜利,甚至战胜过葡萄牙舰队。但是致力于陆地的北京政府从未批准建立常备水师,而且常常解除那些参加海盗活动的水手的武装,以此证明官方不承认海军的合法性。
明朝政府最终以完全传统的方式灭亡。与一位明朝将军里应外合,1644年,以帮助镇压明朝国内叛乱为借口,一支来自女真人的强大而纪律严明的军队进入北京。一旦占领都城,女真人就拒绝继续与明朝政府合作。他们自己的首领自称“天子”,建立了一个新王朝——清朝。女真人经历多年战争才巩固他们所占领的中国大陆领土。自称明朝江山支持者的最后一个大本营——台湾直到1683年才臣服北京政权。
在他们以征服者身份进入中原之前,女真人就已经相当熟悉中国文明。与蒙古征服中原地区给蒙古文化打上烙印不同,没有来自西亚的外来色彩可以防止新主人顺利而迅速地继承中国文明的传统。但是女真皇帝不信任汉人的忠诚,力图把军权掌握在他们自己的人手中。因此,女真士兵都驻扎在中国各个战略要地。他们穿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保持自己的行为习惯,因为这变成了保持士兵不与汉族人口自由通婚的一个政策。但是,民事管理利用汉族和满族,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传统科举取士方法继续实行,除了偶然的和地方性中断外。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这种从一个王朝到另一个王朝的顺利过渡也是罕见的。此外,满族皇帝的行为完全是传统的。他们的主要精力和军事力量都用于保卫中国的领土边境,防止草原游牧民族和诸如西藏那样不稳定的边疆。但是清代中国边界面临一个新的戍守问题,因为他们不仅必须与游牧部落打交道,而且必须与不断扩张的沙皇俄国打交道。应该记住,俄国的毛皮商人在17世纪初就已经把他们的活动范围延伸到西伯利亚,1638年接近了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接着俄罗斯商人力图与西伯利亚森林地区南部草原民族建立关系,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此外,他们开展了与中国的毛皮贸易,中国对貂皮的崇尚犹如欧洲一样。
经过一些为了获得优势的争论后,1689年,两个农耕民族同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两大帝国之间插入了从外蒙古向西到中亚的大部分草原无人区。该条约还规定了管理完善的骆驼商队贸易,以茶叶和丝绸交换毛皮。但是这个条约是不稳定的,因为居住在缓冲地带的蒙古人不愿意充当中国和俄国指定给他们的中立和被动角色。相反,他们与西藏建立宗教联系。这引起中国对新蛮族联盟的担忧,害怕他们成为永志不忘的成吉思汗大军那样的潜在威胁。为了遏制这种可能性,中国开始再次推行一种向前推进的政策,由于俄国军队当时正忙于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战争,所以沙皇的代表不得不静观其变,而中国经过激烈的战争,收复了外蒙古和新疆。西藏接着也归顺了。这些战役直到1757年才结束,在中国军队和天花瘟疫的打击下,土尔扈特部落联盟才瓦解。其残余逃往俄国领土避难,被安置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他们的后裔一直在那里生活至今。30年前,在《恰克图条约》中,俄国人正式默许中国势力非常大范围地穿越几乎欧亚大陆草原的一半。
清朝皇帝在解决海防问题方面同样成功。1636年,为了自身的缘故,日本政府禁止臣民下海航行,禁止建造海船。这就切断了海盗劫掠的主要来源,这些海盗劫掠曾经为害中国沿海一个多世纪。中国政府地方代表与葡萄牙商人社区任命的发言人非正式地签订的协议,起到了抵御劫掠、控制最早的欧洲商船参与大多数非法活动的作用。因此,当中国政府恢复了稳定时,脱离传统守卫海岸的方法就没有必要了。因此,不出所料,在建立海军和加强海防方面,满族人无所作为。他们觉得没必要采取这些措施,事实上也的确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中国的繁荣和保守主义
领土广袤的中国大陆恢复秩序和正常的行政管理,为繁荣的出现提供了有利条件。人口开始迅速增长。美洲传播过来的新作物,特别是甘薯和玉米,使农业地区能够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扩张而增长。与欧洲商人的贸易变得活跃了。葡萄牙商船长期有效地垄断了中国与日本贸易商品运输,因为中国和日本政府都不允许国民建造海船。此外,出口到遥远的欧洲的茶叶、瓷器和其他中国商品也大规模地稳定增长。为了供应这些市场,中国企业家大规模地生产一些比较廉价的瓷器品种。但是由于增加了大量产品,而大大强化了社会的传统结构,所以这种变化仅仅是强化了中国的传统特色。
文化生活证明了中国的极端保守态度。1500~1700年间,中国的任何经验都适应传统学术和敏感性结构。欧洲人固然带来了一些引起学术界注意的新东西。新的地理信息、改进了的天文观察技术以及诸如钟摆那样的新奇装置,这些都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承认。1601年,以博学多才的意大利人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传教士甚至被允许进入北京的皇宫,但是基督教传教士只有在学习儒家学术的端庄外表举止后才能与宫廷学者来往。王朝更替没有长期打破耶稣会在北京的地位。相反,1640~1664年,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与年轻的清朝皇帝建立了不平凡的友谊,对帝国政府的行为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至于全体耶稣会在帝国宫廷的地位,他们对交往的士大夫官员圈子的影响似乎非常小,他们试图向大多数人口传播福音的努力也没有取得成功。
相反,中国学者和缙绅完全专注于古典文献,他们用细致、缜密的考据方法,阐述古代儒家著作的真正含义。一种更无危害的、哲学气息更浓的“汉学”因此出现了,它不鼓励隐喻解释的勇敢行为,而较早的新儒家可以自由地进行这样的解释。
没有必要解释,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拒绝严肃考虑来自遥远欧洲“南海蛮夷”的学术和外来思想模式。当国内组织制度机构运行正常时,何必需要贤明、镇定而负责任的人们在这种琐碎事情上浪费时间呢?当帝国在海外威力强大,国内一派太平、富庶、风调雨顺、人的举止端庄优雅、按照儒家学说的原则组织社会、礼遇那些皓首穷经的人——当所有这些都变成了现实时,为什么还需要任何人都更多地注意外国呢?因此,几乎毫无例外,中国人遵循常识,只是偶然注意一下耶稣会传教士带到中国的新奇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