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将沉醉换悲凉说晏小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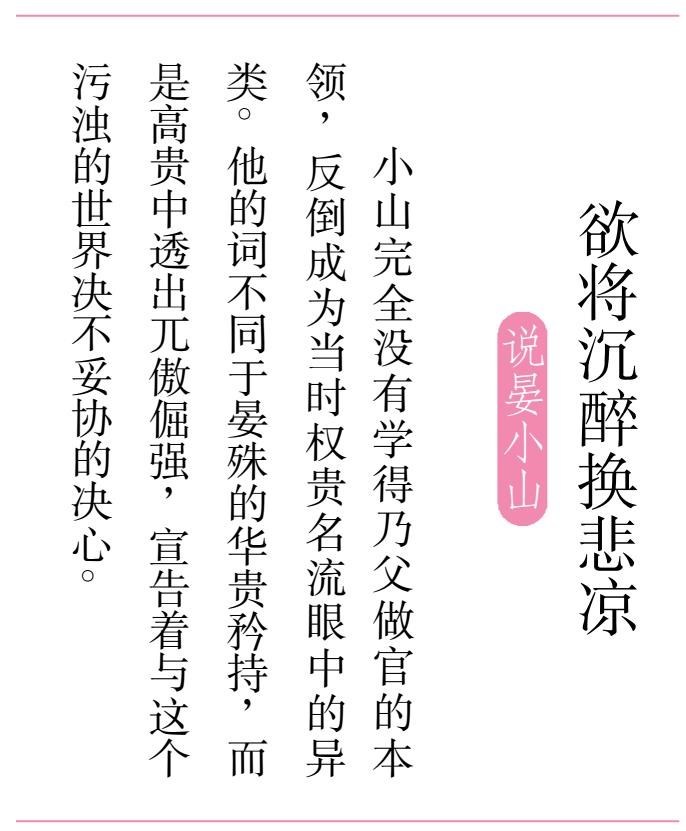

每一个文学爱好者,都会在心里为他熟知的文学家排一排座次,掂一掂谁是状元,谁是榜眼探花。有时候,这种排位只体现评论者的个人喜好,他在说“ 某某是最了不起的大诗人” 时,其实意思是“ 某某是我最喜爱的大诗人”。但如果评论者本身也是行家作手,他的排位就绝不可等闲视之,体现出的实是他的文学观。传统词论家都是词人,他们的意见当然值得重视。对历代词话做一粗略统计,对北宋词人的排位大致分作两派,一派推崇周邦彦,一派则推崇苏轼。
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词集名《片玉集》,又称《清真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评价其集:
多用唐人诗语,栝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
这是从作词的技巧上推崇清真。
陈郁的《藏一话腴》则称:
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知美成词为可爱。
这是自清真词的传播之广、受众之博而立论。
刘肃为陈元龙集注本《片玉集》作序,对清真同样推崇备至:
周美成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缜密典丽,流风可仰。其征辞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历,真足冠冕词林,欢筵歌席,率知崇爱。
旁搜远绍,“旁搜” 是指他擅长用典故,“远绍”则是说他擅于继承唐人的诗风。说他“ 征辞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历”,这简直是把清真比作江西派的诗人。这是针对他的语言风格典雅近诗,以及以学问为词的特点而言。
宋元之际,沈义父作《乐府指迷》,这是一部教人填词的著作,说:
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
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
同样是讲清真的风格典雅,语言醇正。
同时尹焕作《梦窗词序》,则直截了当地说:
求词于吾宋,前有清真,后有梦窗。此非焕之言,四海之公言也。
但对清真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竟然是早年非常不喜欢清真,称清真方诸秦少游,有娼妓与良家之别的王国维。王国维晚年作《清真先生遗事》,直把清真与杜甫并列:
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唯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非先生不可。读先生之词,于文字之外,须更味其音律。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
王国维这样推崇清真,一个原因是王氏本身就不是一位感情丰富的词人,他的《人间词》理致苦多而情致苦少,故对于清真那些淡薄寡情的作品较能赏会;另一个原因则是他重视清真词的音律,却不知词体最初虽是音乐文体,它的文学性还得靠情感的浓挚才得建构。
另一派所推崇的是苏轼。王灼《碧鸡漫志》这样称说:
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王灼的评价,着重在东坡格高调逸,所谓向上一路,指的是东坡对词的内容的拓展。从东坡开始,词就不仅是抒情的文学,更可以用来表现词人的思想。
南宋军事家、抗金名将向子諲 是一位豪放派词人,胡寅为他的《酒边词》作序,有云:
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唐人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胡寅特赏东坡的“ 逸怀浩气”。逸怀是庄子思想的体现,意味着对尘世的坐忘与超越,而浩气则是孟子的精神,表现为对理想的执着坚守百折不回。胡寅认为词到了东坡,则花间词人直到柳永,都只配给苏轼当佣人轿夫而已。
推崇清真的把清真比作老杜。清代刘熙载则以为东坡意似老杜,格似太白,兼有二家之美:
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
而清末四大词人之一的王鹏运,对东坡的评价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北宋人词,如潘逍遥之超逸,宋子京之华贵,欧阳文忠之骚雅,柳屯田之广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虚之婉约,张子野之流丽,黄文节之隽上,贺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拟得其仿佛。唯苏文忠之清雄,夐 乎轶尘绝世,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
王鹏运列数潘阆、宋祁、欧阳修、柳三变、晏几道、秦观、张先、黄庭坚、贺铸的词风,以为虽各尽其美,后人都可得而模仿,唯东坡堪称天才,无从模仿,无从追蹑。他认为词中苏辛并称,辛词虽亦影响巨大,但不过是人中的高境,东坡词却是仙境。他这样推崇东坡词,当然是把格高视作文学评判最高标准的缘故。
我在大学读书时,与同舍友陆杰就曾讨论过宋代谁的词最好的问题。我们观点完全一致,就是认为辛弃疾的词比苏轼的好。我们认为,悲剧是一切文学样式当中最高的文学样式,而辛词中激荡着无与伦比的悲剧情怀,是真正的崇高美,然苏词所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悲剧情怀,因为他的人生观太豁达,悲剧意识就被这种放达的人生观所冲淡,到不了崇高之境。苏词格是很高的,但格高并不是好,真正的好,是能让人感动,是靠执着于人间的悲剧情怀让人感动。东坡什么事都能看得开,面对人生的悲剧现实,他不是选择傲然担荷,而是娴熟地自我排解,这样的人的性情,一定会浮于表面,他写不出最浓挚深婉的爱,也写不出最苍凉沉郁的恨。
而清真的词,我认为一点也不好。单看艺术技巧,清真的确十分高明,他首创了一种蒙太奇式的写作方法,用在长调里,只是通过镜头的转接,就完成了词的叙事,而淡化了时空的顺序,让读者随着词的意脉行进;文辞也典丽可诵,不像柳三变那样,市井气较重。但文学史应该是灵魂的历史,在清真词中,我们见不到感人的力量,因为它们太缺乏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