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记忆:并非个人的历史

谈一千道一万,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很喜欢这句话。
改革记忆:并非个人的历史
假如没有改革
199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周年。
为纪念这一重要的进程,各个新闻单位都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努力做好“改革二十年”的成就宣传。
我们当然也不例外,但总该有些新意,于是在《东方时空》栏目里,我策划、撰稿并主持了后来获得中国电视奖的特别节目《流金岁月》。与此同时,我又担任了《焦点访谈》十四集特别节目《焦点的变迁》的主持人。
几个月的时间里,由于做与此相关的节目,我不停地在改革二十年的时间长河中行走,一幕又一幕或荒诞或让人振奋的历史细节重新在我的脑海中出现。
毫无疑问,改革二十年给中国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了太多的变化,有无数个理由,让我们为这个二十年鼓掌喝彩,即使在其中也上演了我们并不愿见到的情节,但把这二十年,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盛世是不为过的。
不过,在高兴之余,也会时常有一个念头:假如没有改革,我们的今天会怎样?
诱使我不停产生这个想法的一个原因是:在1998年众多纪念改革二十年的书籍杂志中,一本《视点》杂志推出的专号《目击改革年代》里有一篇文章,名字就叫《假如没有改革》。
这篇文章放在这本杂志的最后一篇位置上,其中很多假设让人首先不寒而栗,接着想到这仅仅是个假设又都暗自庆幸。
文章中,列出了一些“假如没有改革”就会在我们今天生活中依然出现的画面。
1.1998年“五一”节,北京市市民凭本供应节日猪肉,每人在原来每月五两的基础上增加三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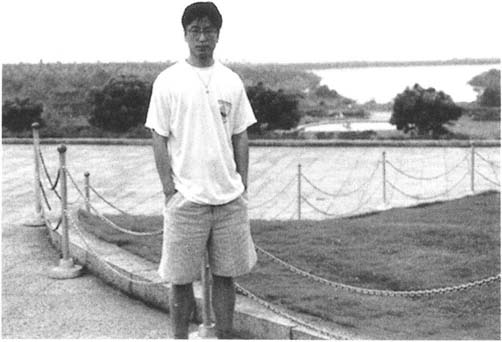
这张照片拍于江西共青城胡耀邦的陵墓,这块陵墓选地很好,胡耀邦的头像正好面对浩瀚的鄱阳湖。
2.热门的职业依旧是司机、副食店职工,大学毕业生最热门的选择是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及其他各级党政机关。
3.1988年大胆提出“多元所有制”的北京大学某著名教授,被开除党籍,发回原籍。
4.“展开穿西装还是穿中山装”的讨论,外交官、电视台主持人仍一律着中山装,间或有些时髦青年以着西装为时尚,于是报纸展开了“我们拒绝没落的生活方式”的讨论。与此同时,由于“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中国大陆首次服装表演被查处。
5.1994年,《北京晚报》登出全国第一则婚姻广告:男,三十岁,身高1米75,副食店职工,父母家有住房。引起轰动。与此同时,离婚率上升,大龄青年、两地分居等问题得到各级党委的重视,并责成各地团委成立专门的婚姻部。
6.1998年1月1日,发表两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刊(《红旗》杂志)新年评论,题为《沿着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勇往直前》,在描述“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之后宣称:东亚经济危机预示着资本主义危机四伏,而在东亚经济危机中,中国依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欢呼“这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明证”,并借此抨击了“那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名义的右倾经济主义的错误思潮”。
…………
这篇文章读到最后,有种想笑又笑不出来的感觉,其实我们每个人还都可以把这篇文章拉得很长。比如,我就和自己玩过这样的假设游戏:假如没有改革,我,一个叫白岩松的人,在这二十年中,会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
1975年,我们城市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我们家门口的广场上出发,我和哥哥都去看了,回来后还在家中议论:哥哥过几年也得下乡,我将来因为是家中老二,因此不一定会去,但读完书该干什么呢?
当时的我还小,似乎被知青下乡的壮观场面所感染,因此家中不管怎样设计,我是小小年纪就打定主意,将来是要下乡的。
可能就下乡了,之后由理想主义到颓废主义,终于吃喝××(后面两个字空缺,因为没有改革,这四个字可能就不全),最后与当地一女青年结为伉俪,开始了漫长的生孩子生涯,时至今日,虽年龄仅仅三十多岁,但脸相上看说是四五十岁也是有人信的。
不过也有可能,我作为家中第二个孩子,躲过上山下乡一劫,在小城之中,我的出路只有一条,中学毕业之后,让妈妈提前退休,然后顶替接班。由于妈妈是教师,而我又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因此当教师的可能性不大,估计是做后勤工作,运气好一些,也可能因自己的体育天分,最后当上了“体育老师”。
也许还有其他的道路,但不管怎么说,我能离开那座边疆小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现在的生活,我的家庭、妻子、儿子都在生活中退出去,一切都是另一幅画面。只不过和今天相比,我会在没什么诱惑的小城里,过着一种没什么幸福也没什么痛苦没什么追求也没什么失落的平常日子。
这样回忆着,就不能不感叹时事造人,1978年的一个重大转折,改变的不仅仅是中国的面貌,更是这其中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今日,原地踏步和一成不变的日子没有了,假设中的一切让人高兴地没能实现。
闲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也不妨都做一下这个假设游戏,想想自己,假若没有改革的话,这二十年的道路会是怎样?人生是不是该用另外的稿纸书写呢?
一定是的。这么一想,今日的很多烦恼就淡了,心情就会好很多。你看,在假设中回忆,有时也是一味药,治现在心中的病。
转折那年,我十岁,我到了北京
1978年我十岁,改革二十年后的1998,我三十而立。
印象太深了,1978年的那个冬天,我正在家中翻阅书籍,我妈妈急匆匆地下班,然后和姥姥在家中连饭也不做就开始商量起来。
原来,我父亲平反了,内蒙要召开追悼大会,我母亲必须带着我哥和我去内蒙西部的集宁市出席这个追悼会。
父亲和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诬陷成“内蒙古人民党”,然后招也得招不招也得招,可父亲还是不招,于是被不停地打来打去,终于埋下后患,在1976年去世,直到死,还都背着“内人党”的嫌疑。从这个角度说,当时的我,也该属于“敌对分子”的家属。
平反昭雪,自然是我们家中的大事,于是我和哥哥都停下课程,从内蒙东部的海拉尔(当时还属于黑龙江省)到西部的集宁。当时没有直达的火车,我们必须先坐车到北京然后再换车到集宁。